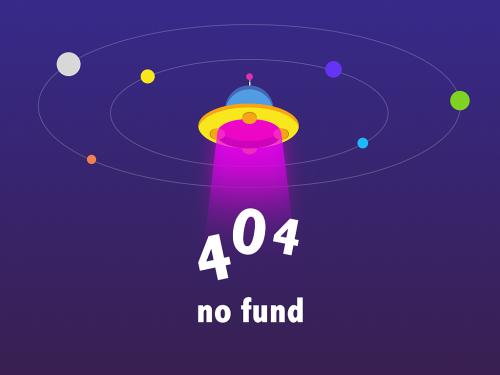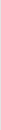关于酗酒者的精神分析
作者:charles melman
原文载于scilicet
来源:心理师
酗酒在ferenzi时代就作为成瘾被定位为某种性倒错的特质,目前无论西方还是国内非禁忌的药物成瘾:酗酒与禁忌的药物成瘾(大麻,冰毒,可卡因等),都是一个越发严重的问题,在精神科也是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此,摘译charles melman关于酗酒者的临床及其处置的文本。
酗酒者沉寂在酒瓶之中,他非常了解自己的真相:上瘾,但是悖论的是,他又选择喝酒以便忘记自己的上瘾。这就是拉康构造的冲动与主体的图示,在对酒精的请求(a的请求)中,在冲动中,主体消失了。
一、现象定位
1被诅咒的转移
我们必须理解酗酒不是原发的,因为原发的问题是他与社会和世界的关系,首先,比如他的老婆,在这里,他的妻子占据了一个核心的转移的位置,因此,他对妻子具有色情狂式的转移。妻子就如同美杜莎,他对于妻子的抱怨就如同那些控制他的那些冲动一样。因此,酗酒者对妻子与别的男人有接触有强烈的嫉妒就不算什么了。
2被侮辱的父亲
酗酒者萎靡的精神以及毫无价值感,回到一个问题:我是自己屋子的主人吗?法则和隐喻并没有建立,一方面,是建立失败的父亲,另一方面是因此产生的全能。这两个以悖论的形式存在,所以酗酒者感受到极易受到侮辱的谵妄形态,但同时,又因此毫无惧怕,充满攻击性。
3嫉妒与真相
这就来到嫉妒的问题上,这里的谵妄并非击中其问题的本质,而恰恰是逻辑的,这和妄想狂是不同的,酗酒者所在的地方,别人遮掩了信纸、话音中断等等现象,“别人因为我而如何如何?”但这本身是逻辑的,如果我们看到酗酒者那醉酒和攻击的暴力,因为他人不知道他的出现会发生什么,所以他观察到的这些反应是逻辑,而非单纯的谵妄。妻子不知道他会怀疑自己什么,孩子也不知道父亲今晚会不会发作。
这样的家庭固着在一种受虐的幻想中。酗酒导致的性无能会加重对妻子的怀疑:对自己的无能进行投射变成妻子的出轨。
4享乐
在酗酒者那里享乐成为核心,由于这种问题,酗酒者对医生是不买账的,医生建议这样那样,因为医生把本质看成是酒,而实际是享乐的议题,所以酗酒者不会把医生制定的规则(父亲的功能)当成一回事,酗酒者的困难本身是与母亲的未分离导致的享乐,和对父亲的排斥。在这个问题上,酒瓶就如同倒错者的倒错客体一样迷人;而另一方面,酒瓶的酒水如同癔症的口欲期的乳房一样。但是我们要区分一下,对于酗酒者,是没有癔症患者对口欲之物的厌恶的,这本质仍旧是父亲的功能缺乏,他不会因为酒而引发癔症的恶心和呕吐,他的呕吐本质不是精神的。
5大他者阉割的否认(disavowal)
妻子,如同原初母亲,作为女性的大他者在酗酒者那里是全能的,他者以吸血鬼的方式呈现,别人都背叛自己!而由于对父亲的功能:法则的大他者——即阉割的否认,他以酒精后的雄性特质去攻击,在二元的关系中,这就是一种主体的悖论:自己成为了超人,回家打女人。在和孩子的关系中,自己作为父亲也无法占据父亲的功能,而是和孩子处于竞争的关系,因此,孩子也被殃及。
二、临床:
我们如何能在治疗中不失败呢?
医生不能成为酗酒者的对象,他们不喜欢医生。这个意义上,酗酒者对于真相的理解:自己的上瘾,会让分析家更易于和酗酒者工作,因为分析家也不固着与确定性上,而是位于偶然和真相的位置去倾听。
但是仍旧是有困难的,由于符号的缺乏,我们不能如同神经症那样去工作,第一个困难因此是酗酒者围绕着想象的阳具,呼唤并且确认雄性性而公开藐视女性的阉割的矛盾,二者导致了酗酒者时不时的同性性行为,在那里被动和主动是一样的。
那么,酗酒者到底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症抑或倒错呢?
继续追问阳具的问题,在那里,这种阳具和母亲粘连,即成为某种乳房的口欲性质,或者准确地说,如果不减缩为客体关系的话,乳房被阳具化!
于是我们就引入了焦虑的位置,酗酒者无法离开酒瓶子,这会焕发焦虑,而酒瓶如同乳房一样,在酒吧间,激发了某种倒错的尊严。酗酒者喝酒如同一种对大他者的效忠,在这些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酒精的生理问题,酒精的效用导致了某种生理的麻痹,主体消失了。这种状态如同一次小小的死亡,因此,酗酒者在这个意义上表现是不尊重生命,不害怕死亡,某种“勇气”;进而是暴力性;同时,主体的消失,让某种大他者上演,他絮絮叨叨的话语非常地快速,对着他人激烈而不断地讲。在身体的维度,皮肤的瘀斑、大出血、发抖也不为所动,他们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对生命毫不在意。而其懒散的形象,自己毫不在意,或者说不知道,这也表明他们对于欠大他者的债务拖欠着,通过其对阉割的否认。相反,他总能从别人那里,甚至陌生人那里挑出各种毛病。某种妄想性质反转的东西产生,“他们拿走了我的一切。”
我们如何进一步定位这些呢?在大他者阉割否认,并处在享乐困境的主体消失中?他无意识地处于女人的位置: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阉割的,所以他们如同女人一样在清醒的时候要戒酒(如同节食),为了法律而保存生命(医生的告诫,某种大他者的法则)。然而,在意识中由于否认阉割而处于父亲的位置:只有一个人没有被阳具法则限定,雄性性质上演。
因此,在临床干预中,除非他认识到这种原始父亲的位置有点过分了,否则治疗是没有可能的。直接限制酒精,则会引发这些本质的问题,加重焦虑和嗜酒!
转移关系则会使得大他者复活,其毫无基础会引发焦虑和去人格化。分析家如果沉默,他会感受到无能和挑衅;而好心的干预则会让对方希望要“更多”而引发异化。在调整异化的构建以及恰当的分析关系下,会引发病理的原发性焦虑:这点他必须放开来,如果可能的话。
对身体和生命的不尊重是精神病的特征?对酒精的成瘾如同倒错?口腔的快感如同神经症的固着?这些问题将继续伴随我们的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