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心理热线010-51296476
公益心理热线010-51296476
 公益心理热线010-51296476
公益心理热线010-51296476
关键词:
来源:
发布时间:2018-0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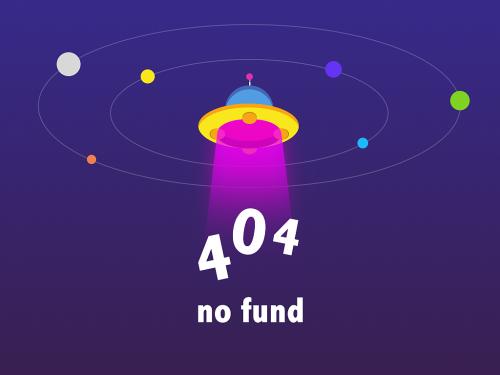
雅克·拉康的他者理论实在是一个解读人类本性的有力工具。他本人自称是弗洛伊德精神的诠释者,然而实际上他所创立的理论则是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颠倒,根本症结在于对人的认识。弗洛伊德从根本上来说是相信人有主体性的,而拉康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从他的“镜像阶段”到“大写他者”,拉康证伪了人的主体性。这意味着,人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作为“自我”而发言的,人从来只是作为“他者”发言的一个载体而已。既然人不可能作为自我发言,那么该如何对人进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医师该如何治疗他的病人,既然他嘴里说着所谓“他者”的话?
尽管从拉康意义上看,自从婴孩从镜子里辨认出一个虚幻的自我形象时,主体就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对人进行精神分析是可能的。因为他者已经融入灵魂,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甄别他者的存在方式,从而找到他者通向正常状态的轨道。
电影是虚构的艺术。没人会说他相信电影中发生的事件,除了不明所以的处在幼儿期的孩子。那么,对于电影中的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是否可能?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体系是临床性的,也就是说他针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病人,并不是艺术世界中的虚构人物。看起来面对虚幻世界中的人物,精神分析似乎无力招架。但是从根本上而言,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工具,它具有其普遍的意义。不管是作为实体的人,还是作为虚构的人物,这两者之间总会有着内在的共性存在。只要是对生活和生命有着深刻洞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总会同现实中的人有着共通的灵魂。
因此可以说,精神分析的方法作为一种心理解剖工具,它同样也适用于电影艺术。
那么,哪些电影先天具备精神分析的可能呢?
《黑天鹅》是一部惊悚片。巧的是,惊悚片是个极为适合精神分析的电影类型。希区柯克的电影已被人分析了无数次,齐泽克还有专著《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的确,惊悚片因为直接面对生命中的恐惧,就像情色片直接面对性一样,具备了可被进行分析的先天条件。
过于强大的母性力量
很明显,我们要找到主人公妮娜的性格形成的根源。她在影片一开始是一个单纯,懦弱的乖巧女孩,到后来她的邪恶蜕变,全都有着其心理学上的依据。关于影片《黑天鹅》的分析倒是有不少影评倒是有不少从精神分析角度出发,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妮娜性格形成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影片中的母亲形象必须予以重视,她从根本上影响了妮娜的性格。
此片令我联想到迈克尔·哈内克的一部作品《钢琴教师》。两部影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它们当中都出现了一个象征意味浓厚的母性形象,这个母性形象超出了正常的秩序,即她们直观上看来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即那是一个过于强大的母性形象。
而我们看到了在这种过于强大的母性形象对于主人公的性格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很明显,母亲欲将女儿据为己有,或者换句话说她们过于恐惧女儿的离去,于是我们看到了《钢琴教师》中的女儿尽管已是中年妇女却还是单身,而《黑天鹅》中的妮娜也已是28岁,她们都和母亲住在一起。而她们都有一个明显的性格缺陷:过于纯洁。如果她们是孩子那么纯洁是个好事,然而她们已经过了纯洁的年纪,再表现出纯洁就是过于幼稚,我们就只能视其为人格缺陷了。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蕴含的精神分析逻辑是父性(母性)力量软弱会造就一个强大的有控制力的子辈形象,条件如果相反,则结果亦相反。这和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如果一个人的家庭生活过于不幸,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有两个发展的面向。一个面向是发展出畸形人格,甚至会发生自杀的行为等,另一个面向是他克服了第一种可能从而发展处超过常人的过于强大的性格,而这种人往往有所成就。
回到影片中来,很明显,那是一股过于强大的母性力量,所以妮娜过于软弱,过于幼稚。她想要获得“黑天鹅”的性格面向就必须完成蜕变。
母亲性格分析
我们都知道母亲表现得蛮横霸道,仔细看,母亲是一个画家,而她的画里面的内容竟全部是女儿的形象。她的意图进一步彰显。
分析母亲形象的关键点来自于一句台词,那是妮娜和母亲的一次谈话中(发生在第55分钟),母亲在询问妮娜教练有没有占自己的便宜时,她有意说出的一句忠告性话语。这句话是“我只是不想看到你重倒我的覆辙”。这句话点名了母亲曾遭遇到的经历,她极有可能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之后就被他抛弃了,而这个男人就是妮娜的父亲,在影片中并未出现的形象。当然了,母亲不想同样悲惨的经历发生在女儿身上。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那么强大,只能理解为她太依赖女儿了,她认为除了女儿之外她一无所有,因此她要将女儿牢牢掌握。
实际上那是一种转移,过于创伤以致无法承受就必须要进行转移,否则可能会精神失常。对于母亲而言,曾经抛弃她的男人让她的精神深深受挫,而她要从一种创伤性经历中恢复的话,就必须找到一个将创伤转移的方法,很明显她的方法就是牢牢掌握自己的女儿命运。
妮娜的蜕变
妮娜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而影片中她要完成的任务是争取到扮演黑天鹅的权利。黑天鹅和白天鹅的对立正好像是人的两面,但是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妮娜可以看做是白天鹅的化身,她纯洁美丽,而黑天鹅魅惑邪恶,这正是妮娜缺少的性格面,于是追寻这个面向成了妮娜的头等大事。很显然,这一过程不可能风平浪静,相反惊心动魄。妮娜从白天鹅到黑天鹅蜕变的过程则是一次拉康意义上完整的异化之旅——他者完全篡位(从主体),从而自我变成了他者附身的躯壳。
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是从一次误认开始的,即婴儿将镜中形象误认为自己,婴儿并不知道那只是自己的虚幻表象,一个来自虚无飘渺的镜中之城的幽灵,相反,他确确实实感觉到那就是他自己。从而人生中第一次异化就完成了,他者篡位成功。
而随着人的不断成长,我们并不仅仅从镜子中寻找自我虚幻形象的认同,而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父母第一次将世俗世界的繁文缛节带给自己,例如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就被父母扔到学校去,而真正想要上学的孩子却没有几个。来自父母的“命令”让孩子第二个层面的异化开始并完成。
第三个层面来自于大写他者的威胁。大写他者来自于想象域。我们在获得了一定的人生积累之后就有了自己的目标,例如孩子们的理想一般都是科学家。而这个科学家的所指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大写他者,他完成了对人的第三个层面的异化。这种异化仍然不是主体的主动性行为,而是一种来自“他者”的命令。
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异化之后,人彻底丧失主体性,从而也就彻底成为了社会性动物。
而妮娜是一个未完成第三个层面的异化的形象,也即她未被彻底社会化。她的艺术人格远远大过她的社会人格。她第一次被一个角色吸引,这个角色成了她欲望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欲望的对象,这个他者指的是她的母亲),于是影片当中妮娜要疯狂追求那个黑天鹅的角色,这个角色本身同她的人格相敌对,为了得到扮演黑天鹅的机会,妮娜必须完成一次彻底的异化之旅。
我们知道异化实际上是通过“误认”来达成的。婴儿误将镜中虚像当做自己,我们误将他者的命令当做自我的需求,在影片当中也多次出现了误认的情境。
妮娜在过道上将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女人误认为自己,一个电影化的表达即是那个女人的脸在镜头里就是妮娜自己的脸,而那个女人就是妮娜要追寻的“黑天鹅”面向的一个初级符号,至少她比自己更富诱惑力。这是黑色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在和她的芭蕾舞同伴莉莉(一个性感的符号)外出约会后,她误认了一整个情境。这个情境竟然是她幻想出来的,也即她竟然和莉莉发生了性关系。这次误认完全是一次想象领域的误认,而这次误认显然又比第一次在过道上误认的形象更进一步——妮娜虚构了整个场景。她离自己的目标又进一步。
结尾高潮部分的《天鹅湖》演出阶段,她视莉莉为一个威胁——她很有可能取代自己。而邪恶的一面在这时候才真正爆发,她在虚构的情境中杀死对方,让自己真正成为“黑天鹅”。到结尾我们都明白了,那个被杀死的人是自己,那个有着邪恶一面的自己。她通过杀死虚构情境中黑天鹅的化身而成为黑天鹅,这是能够让她出演黑天鹅的唯一方式。
因而,通过不断的误认,人在不断地“成长”和变化。在电影中,人物通过“误认”达成了自我的超越。
不可能摆脱的他者幽灵
终于,妮娜完成了一次绝伦的表演。而至此,她真正蜕变,同时也被他者幽灵深刻附体。
结尾处有一个很关键也很迷惑人的镜头,母亲竟然也出现在了观众席上,她满含热泪地看着女儿的表演。这在理性上是无法解释的,母亲不可能出现在那个地方。所以唯一的解释是那是妮娜内心反射出来的虚像。可是为什么在她最为得意的时刻竟让你出现了那个不可理喻的母性形象?精神分析提供的解释则是那是妮娜一直难以摆脱的他者幽灵的复现,母亲就是一个幽灵,她即使不在场,也在精神上影响着妮娜。母亲被安排在了观看者的位置上,意味着妮娜的表演完全是为了给母亲观看。这必然让一般人难以接受,可是精神分析的力量就在于此,它看到了正常规则里的猫腻,它能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
妮娜似乎有着自己的追求,然而那已然是被母亲设定好了的,是母亲送她去学习芭蕾舞的,出演黑天鹅与其说是自己的愿望,倒不如说是母亲的愿望。关于这点,联系下现实就能理解了。
我们在做一件事时是不是觉得某个地方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自己,那就是他者之眼,难以摆脱的幽灵之眼。影视作品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在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后仰望天空,对着自己母亲或父亲已经死去的灵魂说,你看到了吧,儿子(女儿)已经完成了您的夙愿,我没让您失望。
而妮娜在完成了他者的命令后则也变得虚空,那个自残性质的伤口让我们为她的命运担忧,她是否还能再次站在舞台上?
人生就是舞台,观众就是他者。我们的表演本质上是他者命令的复现,如果没有观众我们将也失去自身。某种程度上,这是个悲剧性的局面。
齐泽克说过,今天人们的问题不是太相信虚构,而是恰好相反,不相信虚构。因为不相信虚构,我们错过了认识自身的机会。他认为电影是真正有用的地方就是它提供了一个个虚构的情境,这些情境虽然难以在现实中发生,然而却投射着我们的恐惧和欲望。他也成为了少数将电影视为研究人类本性的思想家之一,我认为,他的判断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心之爱心理咨询工作室搜集整理